推書No.37 史明智《長樂路: 上海一條馬路上的中國夢》:最美的夢,是最殘忍的承諾
不同於電影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中,進入被封鎖的光州,將血腥鎮壓的史實公諸於世的德國記者辛茲彼得,
本書作者史明智,是位美國人,以財經記者身份旅居中國上海六年後,以自己居住的長樂路為軸心,書寫大時代的解與結、小人物的哀與樂,以及折磨他們的生命際遇。
每一篇讀來都十分親近,生動對話下,隱隱浮現人心的光與暗,
筆觸鋭而不尖,像是一把解剖刀,輕輕地慢慢地將虛假的面具剝除。
他第一次來到中國是在二十世紀末,印象最深刻的景象是小鎮上的紅色標語:「女孩也是人」,用以警告因重男輕女而默行殺嬰傳統的務農家庭。
十五年後,二〇一〇年,他舉家搬到上海,迎接他們的是世界博覽會的官方吉祥物:海寶。
十八個月大的兒子激動地朝海寶揮著手,
「那是海寶。」史明智告訴他。
「海寶......海寶!」那是兒子第一個學會的中文詞彙。
這年,上海世界博覽會的宣傳標語是:「城市,讓世界更美好」。
他們所居住的長樂路上,有一間叫做「你的三明治屋」的店,店長是自稱CK的陳凱。
CK出生於一九八一年,一胎化政策執行的第二年。作為家中獨子,備受期待的同時,也肩負莫大的壓力,最大的壓力來自於家庭。
他的父母成長於毛澤東掌政時期,成長過程隨處都是共產黨的口號標語,仰賴家庭或國家指引人生方向。
「體制不讓人選擇自己的職業,不褒揚有才智的人,不鼓勵個體表現,不能在體制內超前別人。」CK的爸爸說道。
那時代的人們要能生存,需自帶某種適應政治環境快速變動的能力,以及受困於洪流,卻能忍住逆流而行的想法。
二〇〇一年,中國加入世貿組織,一生仰賴政府的父母突然迎來新中國,被迫從國營企業中提早退休或裁員,指望CK提供穩定的經濟支援。
此時的CK已然了解到,體制如同爸爸向年幼的他解釋的一樣,它的存在是為了限制、控制你,而非幫助你學習及成長。
但隨著年紀增長,爸爸愈來愈在意金錢及體制提供的穩定性。
他突然變成體制的擁護者,「為政府工作前途無量」總是這樣對CK說。
比起上一代,CK這一代中國年輕人面對無比豐饒的機會之海,他擁有更多選擇的自由,能為自己人生做許多決定:宗教、職業、居所......。
「其實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。我總是想進一步探索自己,想了解自我更多。」CK說。
以前不能做的,現在都可以了。但問題是他們似乎沒有變得比較快樂。
這是所有世代的人們都要共同面對的事情:嘗試去過自己想要的人生。
但要如何做呢?
首先讓我們翻開表層,抽掉一張張以國家社會層層組織所架構的網,從個體的思想、情緒、習慣與反應出發。
你看見的是怎樣的光景?
「等我們長大之後,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呢?」年少時的疑問,幻滅與憂傷永遠是青春歲月裡的一段音節。
儘管看清現實後,就很難再做美夢了,
但今日,數以千萬的中國人白手起家擺脫貧困,放眼望去是新興高樓連成的天際線。
想追求成功的異鄉人日夜湧進大城市,來自山東礦區的趙小姐就是其中一人。
趙小姐出生於貧窮的一九六〇年代,直到他們的青少年時期,中國經濟才開始起飛。
與此同時,貪腐是每天都能見到的現實。因此他們習慣把焦點放在短期獲利,尤其是如何讓下一代過上更好的生活。
「血脈」是命運嵌在她身上的永恆框架,
她需要脫掉這一層皮,赤身重新尋找安身立命的歸屬。
從工廠女工到花店店長,她用了十多年,終於在上海有了一小片立足之地,
但這個在大城市成功的夢想,卻始終掙脫不出一個緊箍咒:體制。
許多人都知道,中國的高考與古時候的科舉制度一樣,具有翻轉整條血脈宿命的功效。
但可能有些人還不曉得,其中有條隱藏的規則:中國政府規定,如果要參加大學入學考試,就得在戶籍地報名,並要求學生就讀戶籍所在地的高中。
這個制度其實其來有自,也就是所謂「戶口」的國家戶政系統。
戶口系統的建立是為了徵收稅金、確保年輕男子入伍服役、監控潛在的社會與政治亂源,以及建立計劃經濟體系,
因而創造出兩個中國,一個城市,一個鄉村,也就是說,農村戶口在大城市毫無價值。
鄉村人如果想申請結婚證明、護照或健保,一定得回到原居地,
這對下一代造成的影響確實不小,
許多孩童在城市出生長大、就學、交友,但戶口還在鄉下,當他們要讀高中時,就被迫搬回父母的出生地,
趙小姐將長子大陽從煤礦小鎮接到城市同住,以為命運就此翻轉,卻在高中入學前被告知,如果要參加高考,大陽得回到礦坑生活。
不斷重複的惡夢,沒有完美的解答,只能努力的面對。
天色未亮,生活還在繼續。
每個人都是這樣努力地活過來,
「隨便找一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聊聊,你就會知道,我們的故事都一樣。」
沒有公平獨立的司法系統,沒有對抗體制的勇敢,沒有個人基本生存的安全感。
這是一個中國到處都有人發夢的時代,但諷刺的是,政府的夢想常常阻撓個人夢想。
「政府口中的中國夢,到底是誰的夢?他們只想讓我們繼續作夢。」
眼看許多中國人迷茫、不安、難過、失望,
作者史明智僅僅是位外來者,不管對歷史與政治議題了解得多深入,終究無法切身感受。
但他隱隱感覺到,這種種個人的情緒背後是一個個未被知曉的故事。
所以他從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現象出發,從「那是什麼?」「為什麼會這樣?」一層層挖下去,
這本書與其說是歷史、是紀實,更像是一次次的提醒:試著用不同世代的眼光去探究此刻的中國是什麼模樣。
作家鍾文音曾寫道:「記憶,從來都不是單一口味的酒,它是成分總無法解析的酒。」
有些事,唯有在結束後才能真正理解。
我一直認為,寫作與閱讀的目的不在於回到最初理想的狀態,而是校準個人與事件的座標。
每個人都努力想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,每個人都折射出可貴的靈魂,
即使被生活摧毀了精神,即使現實吞沒了可能,最後總在絕望之餘,又讓我們看到一些新的希望。
如同土地不語,只是靜靜地等待著下一次的輪迴新生,
所有的終章,其實都只是下一次序曲的前章。
這些人故事結束時,日光再次爬上圍牆,將他們的名字掩埋。
每一位讀者,作為少數的見證者,
都將擁抱著他們的故事,或者被他們的故事擁抱著,
還有餘力作夢的人們,拾起追求夢想的工具與自由,
一同嘗試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,即使錯誤了,至少也可以知道怎樣更接近對的,
繼續向前,嶄新且正確的變化才會有抵達終點的一天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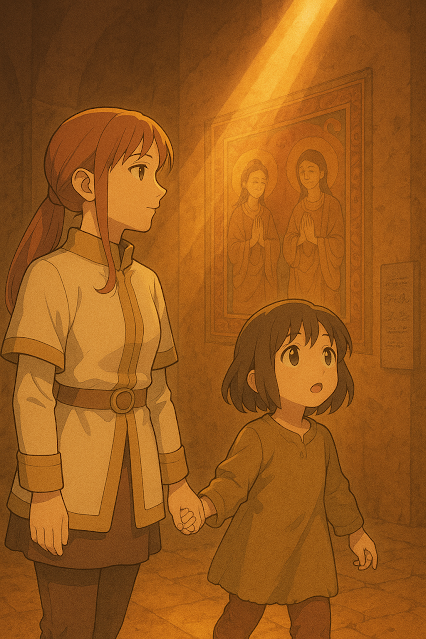
留言
張貼留言